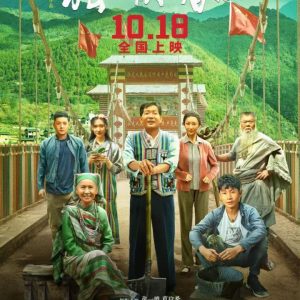《我仍在此》:第97届奥斯卡国际影片奖得主引进确认!
百度云链接: https://pan.baidu.com/s/n5xxv6t7ry6aRL5xT4Y644m
## 破碎与重塑:一位母亲在巴西军政府时期的生存史诗
“妈妈,爸爸还会回来吗?”小女孩蜷缩在沙发一角,手指无意识地绞着褪色的裙边。镜头缓缓推向费尔南达·托里斯饰演的母亲玛利亚,她正在厨房剁洋葱的手突然停顿,刀刃在木砧板上留下深深的刻痕。这个发生在1971年里约热内卢普通公寓里的瞬间,拉开了《我仍在此》震撼人心的叙事帷幕。
沃尔特·塞勒斯的镜头像一把精巧的手术刀,剖开巴西军政府时期被遮蔽的民间创伤。当玛利亚的丈夫在某次”例行问话”后消失,警察送回来的只有沾着机油的外套和半块被压碎的怀表时,托里斯用颤抖的嘴角和突然挺直的脊背,演绎出比嚎啕大哭更具穿透力的绝望。她抱着丈夫的衬衫在浴室地砖上蜷缩成胎儿的姿势,花洒的水流冲刷着瓷砖上晕开的睫毛膏,这个长达三分钟的独角戏让威尼斯电影节的评委们集体起立鼓掌。
军政府的阴影在影片中具象为无处不在的声响:深夜楼下的刹车声、电话突然的忙音、邻居家电视机里突然调高的新闻音量。蒙特内格罗饰演的婆婆总在阳台上晾晒永远干不透的床单,那些湿漉漉的白色织物在风中鼓荡,像极了他们被监控的生活。有场戏令人脊背发凉——玛利亚在菜市场挑选番茄时,发现每个摊主都在重复同样的价格,而角落里穿棕褐色风衣的男人,正是三周前带走她丈夫的其中一位。
但这不是部单纯的政治控诉片。当玛利亚在贫民窟的洗衣店找到工作,摄影机跟随她青筋凸起的手臂在肥皂水中起伏,那些被军警踩碎的尊严正随着衬衫领口的污渍一起褪去。她偷偷收集客人遗忘的纽扣,在阁楼地板上拼出女儿的名字,这个细节后来成为奥斯卡评委会特别提及的”年度最动人电影时刻”。有场戏她被迫为军官太太熨烫真丝衬裙,蒸汽氤氲中闪回丈夫教她跳桑巴的画面,托里斯眼中刹那的柔软与决绝,让观众看见灵魂重生的全过程。
赛尔顿·梅罗饰演的地下印刷工若昂带来转折。在他堆满油墨桶的密室里,玛利亚第一次看到记载丈夫遭遇的传单。那个雨夜她疯狂奔跑在螺旋状的下城阶梯,手提箱里装着违禁的印刷品,军靴声与她的喘息在潮湿的巷道里形成恐怖的回声。当探照灯扫过她藏身的拱门时,银幕前的观众几乎停止呼吸——直到她摸到口袋里女儿梳头时掉落的发卡。
影片最震撼的力量来自对”日常抵抗”的描摹。玛利亚教会女儿用跳绳暗号判断家门口是否安全,在炖菜里藏匿联络字条,甚至用晾衣绳的排列传递信息。有场看似平淡的早餐戏,她边切面包边听女儿结结巴巴读课文,突然把餐刀插进木头桌面——原来课文正是军政府篡改的历史教材。这种克制的愤怒比任何口号都更有力,难怪原著作者马塞洛·鲁本斯·派瓦在首映式上哽咽着说:”这才是我们记忆中的巴西。”
当故事推进到1974年,玛利亚在狂欢节人群中认出那个风衣男人。她涂着夸张的金色眼影,羽毛头饰随着桑巴节奏颤动,慢慢贴近目标。此刻电影突然消音,只见她鲜红的嘴唇开合,男人表情从困惑变成惊恐——没人知道她说了什么,但接下来三年军政府档案解密时,这个官员的忏悔录里反复出现”洗衣妇的诅咒”字样。
影片结尾处,已成年的女儿在1990年的民主广场上,看见白发苍苍的玛利亚正教孙女用纽扣玩拼图游戏。祖孙三代的剪影与广场上巨大的”真相与和解”横幅重叠,远处有人弹起走了调的《来自伊帕内玛的女孩》。这个长达七分钟的固定镜头里,没有台词,只有阳光在纽扣上折射出的细碎光斑,仿佛那些未能安息的亡魂终于得以瞑目。
目前国内引进方正在为某些历史场景的翻译注释与巴西片方磋商,毕竟有些隐喻需要结合葡语特定的语法结构。但可以确定的是,当内地观众看到玛利亚把丈夫的怀表零件埋进花盆时,会理解为什么奥斯卡评委会主席称这是”用个人伤痛丈量时代黑暗的杰作”。那株最终开出的蓝色绣球花,或许正是对所有被迫重生的生命最好的致敬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