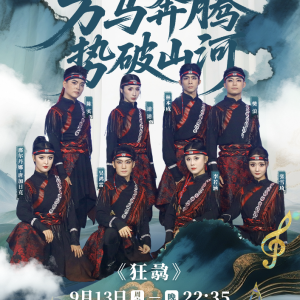《潮》幕后:退潮后,象牙塔能否长存?
百度云链接: https://pan.baidu.com/s/n5xxv6t7ry6aRL5xT4Y644m
## 滩涂上的光影诗篇:当00后大学生用镜头复刻祖辈的围垦岁月
2025年3月2日的萧山夜晚,空气中飘着咸湿的海风味道。中国美院象山校区的放映厅里,银幕上正翻滚着浑浊的潮水,镜头扫过一群赤脚在泥泞中扛石筑坝的身影。当片尾字幕亮起,前排几位白发老人悄悄抹起了眼泪——他们是五十年前真正参与过萧山围垦的”老垦荒”,此刻银幕里复刻的,正是他们用血肉之躯对抗钱塘江潮的青春。
导演万波站在台侧,手指无意识地搓着衬衫下摆。这位浙江传媒学院的摄影系老师,此刻不像平日里在讲台上侃侃而谈的模样。他的长片处女作《潮》刚刚结束首映,台下坐着的不只是普通观众,还有故事的原型人物。”就像把作业交给当年的亲历者批改”,他后来这样形容当时的忐忑。
影片开头有个令人屏息的十分钟长镜头:黎明前的滩涂上,数百个模糊的人影如蚂蚁般在雾气中移动。突然潮声由远及近,人们开始疯狂奔跑,有人被浪头打翻,装满石块的竹筐在浊浪中沉浮。这个画面源自金光炎的记忆碎片——这位萧山籍出品人童年时亲眼目睹过抢险场面,”当时我父亲把麻绳系在腰上就往浪里冲,背后拉绳子的二十多人像拔河一样被拖出去好几米”。
为了还原这种粗粝的真实感,剧组在慈溪真实滩涂上重建了六十年代的堤坝。美术组的同学们连续三周泡在图书馆,把发黄的工程图纸上的毛竹桩、石篱笆等细节——复原。饰演民工的大学生演员们每天收工后,戏服能倒出半斤泥沙,有个女生开玩笑说感觉自己成了”人形沙漏”。
最惊心动魄的是抢潮戏的拍摄。根据潮汐表,剧组只有每天退潮后的四小时窗口期。执行导演王凯旋记得有次刚架好机器,远处突然传来闷雷般的轰响。”所有人都在喊潮来了,我们扛着设备往堤坝跑,回头看见潮水已经吞没了刚才的机位。”这种与自然博弈的紧张感,意外地让年轻演员们进入了最真实的状态——镜头里他们惊恐的眼神根本不用演。
摄影指导周禹帆发明了”水墨纪实”的拍摄手法。他用纱网罩住镜头,让烈日下的劳作人群在逆光中变成剪影,远看就像一幅流动的《清明上河图》。有场夜戏他们意外拍到了萤火虫,这些光点在民工们举着的火把间飞舞,后期时万波坚持保留了这个计划外的诗意瞬间。
围垦亲历者陈阿婆在观影后拉着编剧卢乙莹的手不放:”那个用身体堵管涌的小伙子,和我老伴当年一模一样!”其实剧本里这个情节融合了十几个真实故事。卢乙莹在采风时发现,老垦荒们讲述历史时总爱比划手势,”他们用手掌丈量堤坝宽度,用胳膊演示打桩动作,这些肢体记忆比文字档案更鲜活”。
影片后半段有段看似闲笔:民工们在雨棚里传看家书,有人把腌菜罐子当宝贝搂着睡觉。这些细节来自浙传学生们的集体创作。导演助理凌利在资料馆找到本发霉的工地日记,里面记载着”今日张同志收到妻子寄的布鞋,分给光脚的李同志穿”之类的琐事,”原来史诗是由无数个这样的瞬间编织成的”。
首映礼后的交流环节,有位戴眼镜的男生站起来提问:”你们00后为什么会对这段历史感兴趣?”摄影组的同学举起满是疤痕的小腿——那是滩涂上的贝壳划的,”当我们在同样的烈日下流汗,突然就懂了当年那些只比我们大几岁的青年”。银幕内外,相隔半个世纪的两代年轻人,在这部电影里完成了奇妙的对话。
散场时,万波注意到几位老垦荒站在海报前久久不愿离去。他们用长满老茧的手摸着海报上年轻的演员面孔,仿佛触摸到了自己的倒影。潮水会抹平沙滩上的脚印,但有些记忆,正通过光影的魔法在新时代的瞳孔里继续涨落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