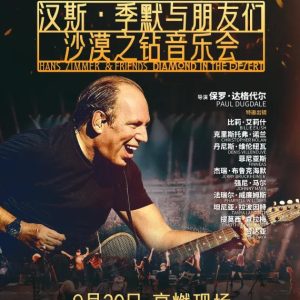《潮》:浙派电影描绘生态文明与历史画卷
百度云链接: https://pan.baidu.com/s/n5xxv6t7ry6aRL5xT4Y644m
## 钱塘江畔的人与潮:电影《潮》如何用影像雕刻一段沉默史诗
银幕上,钱塘江的潮水像一头失控的野兽,裹挟着泥沙与愤怒,一次次扑向刚刚垒起的堤坝。那些用肩膀扛着石块、用双手攥紧麻绳的萧山农民,在滔天白浪前小如蝼蚁。镜头突然切到特写——浑浊的江水漫过一双皲裂的脚掌,指甲缝里嵌着永远洗不净的泥垢。这是电影《潮》里最让我头皮发麻的瞬间,那些在教科书里被简化为”围垦精神”四个字的岁月,突然有了体温和痛感。
这部3月11日在全国艺联专线上映的浙产电影,把镜头对准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开始的萧山围垦史。导演没有选择传统主旋律的宏大叙事,而是让摄影机像潮水一样在历史缝隙里流动。有个长镜头我记到现在:暴雨夜里,上百人用草袋装土堵缺口,闪电照亮他们佝偻的脊背,突然堤坝裂开个口子,所有人像下饺子似的往水里跳,用肉身当沙包。没有悲壮的配乐,只有呼啸的风声和此起彼伏的萧山土话——”夯煞哉!””抵牢!”这种近乎纪录片质感的处理,反而比任何英雄主义台词都更有冲击力。
影片里反复出现的意象很有意思。江平远这个虚构的主人公,总在退潮时独自走在新围的滩涂上,脚下是还在渗水的土地。有场戏是他蹲着观察沙蟹打洞,画外音却是生产队长宣读亩产指标的广播。这种人与自然微妙对峙的状态,被导演用4:3的画幅框住,像极了老照片的构图。最魔幻的是”潮汐之树”那段——枯死的树干在月圆之夜随潮水起伏,树皮上全是贝壳割出的伤痕,江平远摸着树疤说:”它比我们会认潮信。”这种带着民间传说味道的隐喻,比直白歌颂”人定胜天”高明多了。
说到声音设计,《潮》玩得相当大胆。除了必要的对白,大部分时候只有三种声音:潮声、夯土声和人的喘息声。围垦成功的庆功宴那场戏尤其精彩——本该喧闹的场面,导演偏偏让所有欢声笑语渐渐淡出,最后只剩筷子碰碗的叮当声,以及远处始终未停的潮涌。这种留白让人想起《黄土地》里的安塞腰鼓,不过《潮》要更克制些。倒是几段即兴的萧山民谣突然插入时,会产生奇妙的间离效果,就像历史本身在银幕上打了个嗝楞。
北大教授李道新说这片子有”史诗性的悲剧美学”,我倒觉得它更像首散文诗。没有刻意渲染苦难,但那些细节自带重量:母亲用围垦区第一茬棉花给女儿缝嫁衣,线头老是打结;知青在测量时发现水准仪里映出的自己长了白头发;老农蹲在水泥堤岸上嘀咕”土龙(钱塘江古称)被链住了”…这些碎片拼出的不仅是”人类造地史上的奇迹”,更是三十多次溃坝又重来之间,人与自然的某种和解。
影片结尾处有个超现实镜头:已经白发苍苍的江平远走在现代化堤坝上,突然听见身后传来年轻时的号子声。他回头,看见1968年的自己正和工友们扛着石夯走来,两代人擦肩而过时,银幕上响起潮信将至的闷响。这个处理妙就妙在没说透——你既可以理解为历史记忆的闪回,也可以看作土地对征服者的某种回应。就像钱塘江从来不是被”战胜”的,它只是选择了与人类共处的节奏。
坐在影院里,我突然想起小时候在萧山亲戚家见过的老照片。黑白相片上那些面容模糊的围垦者,在《潮》里终于有了眉眼。他们夯土时的喘息、溃坝时的哭骂、收获时憋着不掉的泪,比任何数字都更能说明”为什么这片咸碱地能长出稻米”。当商业片忙着造梦时,这样的电影像滩涂上的芦苇,固执地记录着土地本身的记忆。散场时听见后排观众用萧山话打电话:”爹爹,我在电影里看见阿拉祠堂前的石坎了…”这或许就是方言叙事的意义——不是为了让所有人听懂,而是让该认出来的人一眼就能相认。